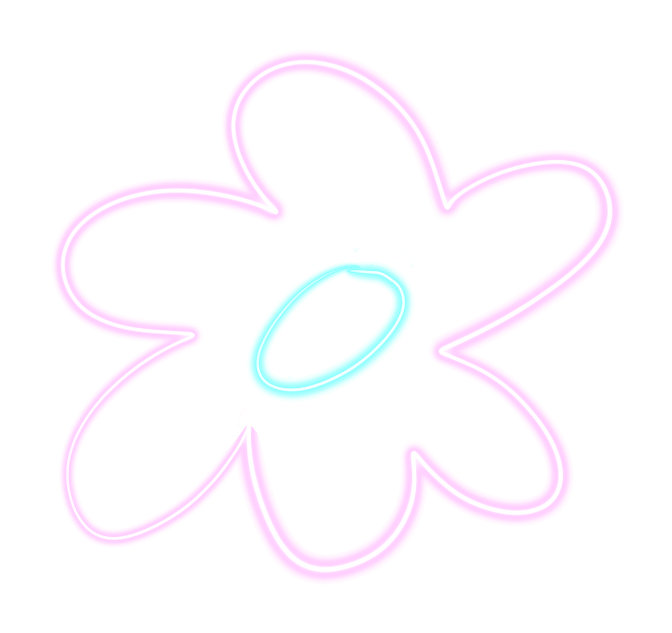走了多久?
一个太阳,一个月亮,一条河,六座山。
有种力量传来了,非常微弱,确凿无误,古阿霞在狭小的船内感受到了。帕吉鲁要她俯身船底去听。她贴上船底。太神奇了,湖里的声音被放大数倍,木船像是听诊器般的完美收音,起初有多种杂音干扰,她继而听到湖水拍打木箱之下的更多声音。有撞击声,也有什么迅速穿过水流的摩擦声。湖泊是活的,属于聒噪要说话的那种,不是一滩水而已。
“湖是巴爹力(BATTERY)。”
“这说法太神奇了,”古阿霞睁大眼,仔细听他讲,然后整理出结论,“所以是这座湖水提供微弱的电力,放大了山的动静,我听到的是中央山脉长高的声音。另外,还有各种湖里活动的声音,那是某种生物吗?”
“也不是。”
她再整理一下,又说:“湖是电池,不只放大声音,也可能储存声音。我听到的可能是某种在湖里活动过的生物?”
“是的。”
“如果那不是鱼,是什么?”
突地,船壳传来轻微的撞击,打断两人对话。古阿霞感到那不是昆虫撞击船舷,是强稳的力道扣响船底。帕吉鲁也是,他对木箱的传音效果有信心。这木箱是云杉,材质轻,共鸣效果好。水底传来的撞击,很清楚的力道,帕吉鲁甚感大惊。不过接下来的长久时间,没有任何下文。
“刚刚是爸爸留下的话,”帕吉鲁说,“他说──咚。”
“咚,好大的一声,咚是什么意思?”
“再美丽的山都会垮掉,再美丽的树都会倒掉,再美丽的鱼都会死掉,再美丽的湖也会干掉。”帕吉鲁讲得很顺,不是练习很久,就是放在内心很久,“美丽的东西却不会在那个人的心里死翘翘,这就是‘咚’。”
“说得很好。”古阿霞鼓励他讲下去。
“湖是巴爹力,也是爸爸的墓。”帕吉鲁不再多说了,话是障碍。风没说过话,山也没有,整个大地没有,却处处充满丰富的言语。